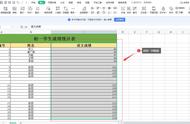今日阅读的《昆虫记》,是(法)法布尔著,王光波译。
第二章
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时代,无忧无虑,几乎和昆虫不分彼此。那时的我几乎和鸟类一样,充满着对鸟巢、鸟蛋和张着黄色鸟喙的雏鸟的渴望。我喜欢把山楂树当做床,把鳃金龟和花金龟放在一个扎了孔的纸盒里,然后放在那张床上喂养。我很早就被蘑菇那绚丽多彩的颜色迷住了。当那个稚嫩的小男孩第一次穿上吊带裤,被那些不易读懂的书籍吸引时,就好像是我第一次发现鸟窝和第一次采到蘑菇时一样激动。人到了晚年,就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现在就让我来说说这些重大的事情吧。
中午时分,一窝小鹑正在太阳底下安静地休息,被一位路过的行人惊吓后,急忙四下逃散。这些小鸟像漂亮的小绒球似的,争先恐后地逃离,转眼消失在荆棘丛中;等四周恢复平静之后,伴随着第一声呼唤,小鸟们又都跑回来争相躲在妈妈的翅膀下。这幅情景唤醒了我那沉睡的童年记忆。我的好奇心开始从那朦朦胧胧的无意识中摆脱出来。在久远的回忆之中,我重新回到了那美好的岁月,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往事就像一群雏鸟,在生活中的荆棘行走时被粘掉了羽毛。有些从灌木中逃出来时头被撞得疼痛不堪,晃晃悠悠的,连路都走不稳;还有些消失不见了,也许已经闷死在荆棘丛的某个角落里:还有些精神依然不错。然而,在记忆里最富有生命活力的依旧是那些最早发生的事。在儿时记忆的软蜡膜上这些事情所留下的印迹,已经变成了青铜般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那天的运气可真不赖,有一个苹果作点心,还可以自由地活动。我打算到附近那座被我当做是世界边缘的小山顶上去看看。那儿有一排树,它们背风站立,就像要被连根拔起飞走似的。它们不停地摇摆着弯腰鞠躬。柔软的脊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今天它们安静地屹立在蓝天下,明天当云飘过时就会摇摆起来。我欣赏它们的淡定,也为它们惊恐不安的样子而难过。它们是我的朋友,我常常都能够见到它们。穿过我家的小窗户,我不知多少次看到它们在暴风雨中频频低头摇摆,看见北风从山坡上刮过,卷起滚滚雪暴,这些树们在被撼动的大地上绝望地摇摆。这些饱受摧残的树在山顶上做什么呢?清晨,太阳从淡淡的天幕后升起,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太阳来自哪里?登上高处,我也许就能够找到答案。
我往山坡上爬去。脚下的草地已经被羊群啃得稀稀落落,幸亏没有荆棘,要不然,说不定我的衣服会被划得破破烂烂,回家后还得为此被家人责问:这儿也没有大岩石,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扁平大石头,要不然,攀登时还可能出危险。道路很平坦,只管一直向前走就是了。但是这里的草地像屋顶那样,有坡度,我得不时地往上看。而且斜坡长得很,但我的腿却很短。我的那些朋友,也就是山顶上的树木,看着也并没有变得近一些。小伙子,勇敢点!努力往上爬。呀,刚刚有什么东西从我脚边经过?原来是一只漂亮的鸟刚刚从藏身的大石板下飞出来。有个鸟窝,是用髦毛和细草编造起来的。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鸟窝,真是太走运了!在鸟窝里共有六个蛋,它们挨在一块儿很好看。蛋壳就像在天蓝色的颜料中浸过似的,蓝得那么好看。这是鸟类带给我的第一次欢乐,我被幸福的感觉包围了,干脆趴在草地上,观察起来。
但就在此时,雌鸟一边慌乱地从一块石头飞到附近的另一块石头上,一边嗓子里还发出塔格塔格的声响。那个年龄时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同情,我甚至对母亲的担忧挂念也无法理解,真是个十足的大笨蛋。当时我的脑子里正计划着想要抓这些小动物。我想在两周之后再回到这里,在这些鸟儿还没长大飞走之前掏鸟窝。不过现在嘛,就先拿走一个鸟蛋,就一个,用来证明我这个伟大的发现。
我害怕会把那个脆弱的蛋打破,便把它用一些苔藓垫着放在一个手心里。童年时没有体验过那种第一次找到鸟窝时欣喜若狂的心情的人们,你们想指责的话就指责吧。我干脆不再向上爬了,下次再去山上看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那些树木吧。我走下山坡,小心翼翼地握着鸟蛋,以免一脚踩空把它捏烂,在山脚下,我碰上了牧师,他边散步边看日课经。他注意到了我走路时那紧张严肃的模样。像是一个搬运圣物者似的。很快,他就发现了我的手里藏着什么东西。
他问道:“孩子,你手里是什么东西?"
我有点忐忑不安地伸开手掌,那枚躺在苔藓上的蓝色的蛋就露了出来。
“啊!这是'岩生’,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牧师说道。
“山上,从一块石头的底下。”
我招架不住他的一再追问。很快就把自己的小过失全盘招认了。我并不是特意去掏鸟窝的,而是偶然地发现了一个鸟窝,那里面共有六个蛋,我就拿了一个,就是这个。我想等其他的蛋孵化,等到小鸟的翅膀上长出粗羽毛管时,再去捉它们。
牧师答道:“你不能这样做,我的孩子。你不该从母亲那里抢走它的孩子,这个家庭是无辜的,你应该尊重它,让上帝的鸟长大,然后从鸟窝里飞出来。它们帮助我们清除庄稼的害虫,是庄稼的朋友,要是你想做个好孩子,就不要再去动那个鸟窝了!”
我答应了。牧师继续他的散步去了,我也回到了家里。那时,我孩童时期近乎空白的大脑中播下了两颗优良的种子。刚才牧师那一番威严的话语让我明白,破坏鸟窝是一种糟糕的行为。虽然我还不知道鸟是怎样帮助我们消灭虫子、消灭破坏收成的害虫的,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已经感到让母亲伤心是不对的。牧师看到我所找来的这个东西时说了“岩生”这个词。瞧!我心想,动物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有名字。“岩生”是什么意思?是谁给它们起的名字?在草地上和树林里,我所知道的其他一些东西又叫什么呢?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拉丁语“岩生”是生活在岩石中的意思。当年,当我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窝鸟蛋时,那只鸟确实是从一块岩石飞向另一块岩石。那个以突出的大石板为屋顶的巢就是它的家,从一本书中我进一步了解到,这种鸟也叫土坷垃鸟,它喜欢多石的山冈,在耕种季节里,从一块泥土飞到另一块泥土上,找寻犁沟里挖出的虫子。后来我又知道普罗旺斯语里它叫做白尾鸟。这个生动形象的名称让听到的人很快就联想到,它在休耕田上突然起飞做特技飞行表演时,那展开的尾巴就像是白蝴蝶。牧师口中随意脱口而出的那个词,向我打开了一个世界,一个草木和动物拥有自己真实名称的世界。有一天,我将用它们的直实姓名,与田野这个舞台上数以千计的演员和小路边成千上万朵小花们打招呼。还是将来再去整理卷帙浩繁的词汇吧,今天我只是先回忆一下“岩生’这个词。
我们村子西面的山坡上,鼓突的矮墙围起层层梯田,墙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地衣和苔藓。那里有层层分布的果园。李子和苹果成熟了,看着就像是一片鲜果瀑布。在斜坡流过一条小溪,无论站在哪个地方都能一步跨到对岸。在水面开阔的地方,有一些半面露出水面的平坦石头,让人们踩着过溪。最深的地方也不会没过膝盖,因此孩子不见时,母亲们也不用担心孩子是否跌落到了深水涡流中。可爱的溪水,如此的清澈、宁静,而又安详。后来我见过一些波澜壮阔的河流,也见过浩瀚无垠的大海,但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能与那涓涓细流相媲美。你是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章神圣诗篇,因此才能在我的心目中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一位磨坊主竟然想打这条穿过牧场的欢快溪流的主意。
他在半山坡上依着坡的斜度开出一条沟渠,让水分流,然后引进一个蓄水池里,为磨盘提供动力。这个水池被围墙围了起来,围墙脏兮兮的,长着蒴草胡须。它所处的地方在一条小路边,那儿人来人往。一天,我骑在一位伙伴的肩膀上,从高处向里张望。我眼前是深不可测的死水,上面漂浮着黏黏糊糊的绿色种缨,滑腻腻的绿毯露出一些空洞,空洞里懒洋洋地游动一种黑黄色的蜥蜴,那时我觉得它像眼镜蛇和龙的儿子,就是我们半夜三更无法入眠时讲的恐怖故事里的那种怪物。现在其实应该把它称为蝾螈。我的天哪,我可看够了,还是赶紧下去吧。
再往下走一段,水汇成溪流,两边的赤杨和白蜡树弯下腰,枝叶相互交错,形成了绿荫穹隆;粗根盘错,盘构成了门厅,门厅往里就是幽暗的长廊,那里是水生动物的藏身所。在这个隐蔽场所的门口,光线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形成了椭圆形的光点,不停晃来晃去。我们悄无声息往前移动,趴在地上观察。在洞里住着红脖子鲢鱼。那些喉部鲜红的小鱼真漂亮!它们腮帮子一鼓一瘪的,没完没了地漱口。大家成群结队,齐头并进地逆流而上。要是想在流动的水里保持不动,就轻轻地抖动尾巴。一片树叶落入了水中,刷!那群鱼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小溪的另一边是一片山毛榉小树林,树干像柱子似的,光滑笔直。小嘴乌鸦在它们茂盛的树冠间呱呱地叫着,从翅膀上啄弄下一些被新羽毛替换下来的旧羽毛。地上铺着一层苔藓,我在这柔软湿润的地毯上还没走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尚未开放的蘑菇,看着就像是随处准备下蛋的母鸡丢下的一个蛋。这是我采到的第一个蘑菇,一种好奇心唤起了我观察的欲望。我把它拿在手里好奇地打量着它的构造,反反复复地看。
没过多久,我又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其他的蘑菇。这些蘑菇形状各异,大小不一,颜色纷呈,有的像铃铛,有的像灯罩,有的像平底杯,有的长长的像纺锤,有的凹陷则像漏斗,还有的圆圆的像半球。让我这个刚刚入门者眼界大开。我看到一些蘑菇瞬即就变成了蓝色,还看到一些烂掉的大蘑菇上爬着虫子。还有一种蘑菇像梨子,这是我见到的最奇怪的蘑菇。它干干的,顶上有个像烟囱一样的圆孔,当我用指尖弹它们的肚子时,就会有一缕烟从烟囱里冒出,等里面的烟散发完了,就只剩下一团像火绒一样的东西。我在兜里装了一些,这样有空时就可以拿来冒烟玩。
我在这片欢快的小树林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自从第一次发现蘑菇后,我又多次光顾,就是在那里,在小嘴乌鸦的陪伴下,我懂得了关于蘑菇的基本知识。渐渐地,我就采了好多蘑菇,但我的收获物没有得到家人的欢迎。那种被称作“布道雷尔”的蘑菇,在我家人那里名声很臭,说是吃了它会中毒,母亲将它们从餐桌上清除了。为什么外表那么可爱的“布道雷尔”,竟会那么危险呢?我不明白。但是最终我还是相信了父母的经验,所以,虽然我莽撞地和这种毒物打过交道,但一直都没出什么事。
我继续到山毛榉树林那儿去。我得找出规律,这样才能容易记住,这就促使我发明了一种分类法。最后我把自己发现的蘑菇归成三类。第一类最多,这类蘑菇的底部带有环状叶片;第二类的底面衬着一层厚垫,上面有许多不容易发现的洞眼;第三类有个像猫舌头上的乳突那样的小尖头。很久以后,我得到了一些小册子,我从那上面得知我归纳的三种类型早就有人知道了,而且还有拉丁语名称。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兴致。拉丁文名称为我提供了最初的法文和拉丁文互译练习,使蘑菇变得高贵起来;这种教区牧师颂弥撒时所用的语言,也给蘑菇笼罩上了一层光辉,它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看来它真的很重要,才配得上有名字。这些书上还写着,那种曾经以冒烟的烟囱引发我好奇心的蘑菇,名叫狼屁。这个名称听着挺粗俗的,使我不太满意。旁边还写着一个体面一些的拉丁文名称,“丽高释东”,但这也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有一天我根据拉丁语词根才弄明白,原来“丽高释东”正是狼屁的意思。植物志里总是保存着大量并不总是适宜翻译的名称。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我们今天的那么严谨,而植物学往往不顾及文明道德,保留了粗俗直接的表达方式。
那段美好的童年时代,对有关蘑菇的知识充满特别的好奇心的岁月,现在已经离我多么遥远了啊!贺拉斯曾感叹,时光飞逝啊!确实,岁月在飞快地流逝,尤其是当快到尽头时。它曾经是快活的溪流,悠然地穿过柳林,顺着几乎察觉不到的坡面流淌着,而今却成了裹挟着无数残骸、奔向深渊的急流骇浪。光阴稍纵即逝,还是好好珍惜利用吧。当夜暮降临时,樵夫急急忙忙地捆好最后几捆柴火。同样,已经垂垂老矣的我,作为知识森林中一名普通的樵夫,也想着要把粗柴捆整理好。在对昆虫的本能所作的研究中,我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事,最多也不过剩下几个已经打开的窗口。窗口所指的那个世界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它正等待着我们的开发。
我自童年起就青睐有加的蘑菇,它们的命运将更为糟糕。我至今依然和它们保持着联系,从来没有断交过。在睛朗的秋日下午,我步履蹒跚地拖着沉重的步伐去着望它们。那些从红色的欧石楠地毯上冒出来的大脑袋牛肝菌、柱形伞菌和一簇簇红色的珊瑚菌,我总是怎么看也看不够。寒里昂是我的最后一站,那里的蘑菇争奇斗艳,令我应接不暇。周围长着茂盛的圣栎、野草莓树和迷迭香的山上遍地都是蘑菇。这些年,那么多的蘑菇使我异想天开,我要把那些无法按原样保存在标本集里的蘑菇,绘成模拟图收集起来。我把附近山坡上各种各样的蘑菇开始按照实际的尺寸绘制下来。我不懂水彩画的技法,不过无所谓,不曾学过的事,也可以摸索着去做。开始可能做不好,但慢慢就会顺利起来。与每天爬格子写散文那份费神工作相比,画画肯定能让人轻松愉快一些。
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几百幅蘑菇图。画面上的蘑菇,不论是尺寸还是颜色都和自然的没有多大差异。如果说我的收藏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尚有不足,但它至少是真实的,因此具有一定的价值。一些参观者纷纷慕名前来,每到周日就有人前来观赏,都是些乡亲。他们单纯地看着这些画,不敢相信不用模子和圆规,仅仅用手也能画出这么美丽的图画来。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我画的是什么蘑菇,还能说出它们的俗名,说明我画得栩栩如生。
但这么一大摞花费了那么多精力才得来的水彩画,将来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也

许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会小心地珍藏我的这份遗物,但是迟早有一天,它会变成他们的负担。从一个柜子移到另一个柜子里,从一个阁楼搬到另一个阁楼上,而且总有老鼠前来光顾,然后渐渐粘上污渍。最后,它会落入一个远房外孙的手中。那孩子会将图画裁成方纸,然后折成纸鸡。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我们抱着幻想、以最挚爱的方式珍惜爱抚过的东西,最终在现实面前,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蹂躏。
,